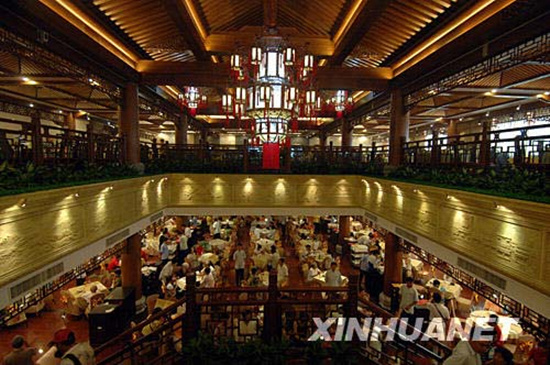
“饮食男女,人之大欲存焉。” 既生而为人,也就未能免俗。“人世间如果有任何事值得我们郑重其事的,不是宗教,也不是学问,而是吃。”林语堂如是说。
吃在北京,在文学的笔端,更是意兴湍飞、摇曳多姿。
老舍说:“秋天一定要住北平。”小白梨与大白海棠,是北平之秋乐园中的禁果,果子而外,羊肉正肥,高粱红的螃蟹刚好下市,而良乡的栗子也香闻十里。
汪曾祺笔下的北京饮食平添了一份追本溯源的认真。
北京人所谓“贴秋膘”有特殊的含意,即吃烤肉。北京“三烤”(烤肉、烤鸭、烤白薯),是“北京吃儿”的代表作。
北京烤肉的起源,难以说清。然而,齐白石写的一块小匾:“清真烤肉宛”,注脚:“诸书无烤字,应人所请自我作古”,却引出古代字书上没有“烤”这个字。朱德熙也给予证明。
梁实秋谈吃,趣味横生,令人口角生津,宛如菜谱,着实可爱。
豆汁下面一定要加儿字。豆汁儿的妙:一在酸,酸中带馊腐的怪味;二在烫,只能吸溜着喝;三在咸菜的辣,越辣越喝,越喝越烫。
烤鸭,在北平不叫烤鸭,叫烧鸭,或烧鸭子,讲究片得薄,每一片有皮有油有肉,若是有皮有肉无油,那你还算不上吃过北平烤鸭。
夏饮酸梅汤,上口冰凉,酸甜适度,含在嘴里如品纯醪,舍不得下咽;冬吃糖葫芦,薄薄一层糖,透明雪亮,用材讲究。
文学里,吃在北京,要科学,要天才,要经验,还要艺术,国人讲究吃,可见一斑。(千龙网评论员 李泽杰)
十月文学月系列评论













